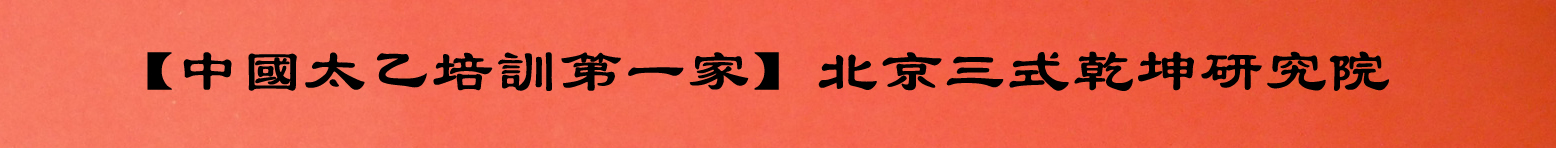时间:2025-08-05
浏览:12778
对话陆致极:知命不唯命
朱蔚 陆致极
朱蔚:这是寻音绕梁的第一期播客,我非常非常开心,可以请到我最想对谈的嘉宾。对命理学感兴趣的人,或多或少都听过这个名字,以及《命运的求索》这本书,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陆老师有趣的人生经历,非常荣幸可以请到陆老师来分享。今天的嘉宾是陆致极教授。
陆老师:大家好,我是陆致极。
朱蔚:我先抛砖引玉,简单介绍一下陆老师的一些人生经历。陆老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在美国的伊利诺大学深造,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所以说陆老师的学术背景非常独特。在他身上,我经常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人文情怀,以及他一开口讲课,就有一种西方教育下学习的一种方法论、数据论、逻辑论,他搭建了一套适合所有人入门的命理学坐标系和命理学框架,同时他用他擅长的语言学的背景,梳理了命理学史的脉络。很巧的是,今年正好是陆老师全身心投入命理学研究的第20年!那我们现在让陆老师讲一下,怎么跟命理学结缘的?
陆老师:我跟命理学结缘,要从1967年春天谈起。对于当时一个68届只读了一年的高中生,究竟我能继续读书呢,还是将来会做什么?确实有点迷茫。当时我有一个好同学的妈妈认识一个盲人算命师。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她把我带到那个盲人算命师家里。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上海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对面的一条弄堂。他满头银发,掐着手指算出了我的所谓“八字”。他说的话,当时我也不懂。因为我当时受唯物主义教育,所以是不信命的。他是宁波人。他说:“哎弟弟,你家里的出身是比较好的。”这个话不仅对我是适宜的,可能对好多的人都是,所以我没有记住他到底谈论了些什么。但是我记住了他最后讲的两句话:第一句,他说“弟弟啊,你回去好好读书,你30岁要好了。”第二句让我特别惊讶,他说“弟弟啊,你将来要出洋游学的。”出洋游学,对当时的我来讲是天方夜谭,因为我们家没有海外关系。这两句话很特别,所以我记住了。十年以后,也就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接着是研究生招考,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我贸然去考了复旦中文系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初试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居然得到了复试的通知。这一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班。这是我人生的根本转折。
朱蔚:就从这一步开始,你的人生发生了第一个改变。
陆老师:是的,发生了第一个改变。1983年我又出洋游学了。我去美国伊利诺大学语言学系,先是交流学者,两年以后我就转入读博士课程,199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所以回想起来,觉得很惊讶,这位老人十多年前的预言居然实现了!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是由好奇而唤起对命理学这门学科的兴趣的。
朱蔚:所以在您当时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命理学的种子。
陆老师:是的。
朱蔚:20年前,您其实是从一个十分体面的工作,直接选择裸辞,全身心投入命理学研究,身边的人有没有怀疑过你做这个选择的正确性呢?
陆老师:有好多年轻人跟我讲,“陆老师你怎么不要饭碗了?”甚至讲,“你怎么来搞这个迷信活动了?”那么,不要饭碗确实是事实,搞迷信倒不是,恰恰相反,是为了破除迷信!
朱蔚:您在这个破除迷信的阶段中,在您还没有任何学术研究前,比如说,还没有写出《中国命理学史论》这本书之前,您内心会不会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有没有彷徨过呢?
陆老师:当时确实没有彷徨过。实际情况是,2006年我女儿硕士毕业,有了工作。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这个经济负担解除了。台湾的梁湘润老师说:“真正要研究命理的人,往往是一种既不是太富裕,但是也不是太贫穷的。他可以有闲散的时间来研究它。”我当时好像也正处在这样的经济状态。我就跟我太太商量,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基本上养老金是有了,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完成我的好奇。命理学和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两朵奇葩,我开始完全是好奇,我只是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是由这个好奇的种子开始发芽的。
朱蔚:您当时著的《中国命理学史论》这本书,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本梳理中国命理传承脉络的书吧?
陆老师:是的,我是07年回国来的。有个朋友介绍我去上海人民出版社认识主编李伟国先生。我跟他讲,想写一本命理学历史的书。我在美国是博士毕业。美国博士的一个基本训练,就说你要写博士论文,你必须了解你这个专题以前人们是怎么研究的。你要先阅读这些著作,因为任何人在学术上的进步都是踩在前人肩膀上的。所以我要研究命理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命理学历史的认识。当时他说:“你这个是搞封建迷信呀!”我说:“恰恰相反,我是要破除迷信来做这个研究的。”后来他说:“那你就去写写看吧。”他以为我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能写出来的。但是我回到美国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把命理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基本上都阅读了,写了中国命理学史论的书稿。08年我拿回去了。
朱蔚:哈哈哈,他怎么说?
陆老师:“你真的做了!”他说。人民出版社没有这样的编辑能够审核这方面的内容,他就把这个书稿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请一个比较了解这门学问的编辑看了。他觉得这本书写的很好,整理了整个中国命理学的历史,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说:“值得出版!”因为他的推荐,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我这本《中国命理学史论》。
朱蔚: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它还有韩文版?
陆老师:对的,2018年,韩国周易学会会长叫金演宰,他把它翻译成韩文了。
朱蔚:是由周易学会会长翻译的?
陆老师:是的。
朱蔚:因为他也比较了解这一块?
陆老师:对,这个人,我看了他的简历,他到北京大学学习过,后来是韩国公州国立大学教授,2018年出了韩文本,是厚厚的上下两大本。
朱蔚:所以这样看来,其实他跟您的学术经历也很相似。
陆老师:所以我确实有点惊讶。还有后来2014年出版了《命运的求索》,目前已是第13次印刷了,读者的反馈极大的鼓舞了我。迄今为止,我已出版了16本命理学的作品,尤其是关于健康研究的。
朱蔚:等会儿我们可以详细聊一下这些书籍。那您会看豆瓣上这些评论吗?
陆老师:我本来不注意。是最近我的学生说:“陆老师你注意下,豆瓣读书榜单上有对你的评论。”那么我看到,是9.1分;还有一本我的教程好像是9.2分。我现在倒是关注它了,因为上面有不少人的评论,有他们的意见,无论是正面肯定还是提出问题,对我来讲都是一种鼓励。
朱蔚:但是你看了他们的质疑,您会高兴吗?
陆老师:我说老实话,我本身是出于好奇来研究这个东西的,并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由好奇进而去研究,由研究进而觉得是一种历史使命,人家的批评若对我的研究有帮助,我当然接受;有些是题外的,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我也作为一种参考。
朱蔚:就择其善者而从之。
陆老师:是的。
朱蔚:这次回国,您有没有发现命理学现在特别火,跟您20年前开始研究的时候完全是两个样子。
陆老师:我因为只是写作,只是教学,或者说,自己也是学生,我并没有形成什么派别之类的。我只管自己的努力,学无止境。但是我去年回来觉得很惊讶,我居然也是这个研究圈子里的一个知名人物了。我确实蛮惊讶的,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一个人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恰恰等收获的时间到了,它自然会来的。这是我去年回来以后的一种感受。
朱蔚:所以您其实默默耕耘了20年。大家对紫薇、八字、包括西占、六爻、奇门这些的命理热,您认为是大家集体一种焦虑的投射,还是说是本身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基因的觉醒呢?
陆老师: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两种情况都有。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精神文明发展的一种诉求,我们必然会召唤自己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命理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你所说的传统文化基因的觉醒,我觉得这样讲法确实也有道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30年来高速成长的国内经济也发生了影响,所以出现了某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于是,这就使预测个人未来的命理“火”起来了。长期以来,算命就有中国式的某种心理咨询的功能。所以你说的这股命理热是集体焦虑的投射,我觉得也未尝不可,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朱蔚:我想到之前王冰师兄说,现在有两种命理师,一种是您要算的准,一种是您能做心理按摩,这两种命理师基本上都能活得很好。
陆老师:是的,命理学从某种意义上,预测人生的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的命理学,它实际上讲究的是一个“变”,对人的心理确实有安慰。为什么呢?人生是变动的,今天不好不等于明天不好,今天有困难不等于明天有困难。所以命理学确实有安抚人们心理焦虑的那种功能。
朱蔚:您刚刚有分享了自己跟命里结缘的经历,在您坐上飞机飞往美国的那一刻您有没有发觉,原来一切都已经被之前的那个师傅说准了,一切都是既定应循的程序。大多数人现在对命理好奇,想了解自己的命,知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命。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其实想让自己过一个更好的人生。您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那如果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人有主观能动性吗?
陆老师:我个人的认为呢,命理实际上是一种先天的趋势,命理所预测的是一个人的概率上的一个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好像是演出剧的一个剧本。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生舞台,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你会觉得同一个剧本由于角色自己的发挥和努力,他的个性色彩,对人物的理解,往往可以演的非常生动。我们不要对命理,单纯的认为就是宿命论,它只是一个剧本或者说是一张地图上的东西。在知命的情况下,你可能更好的发挥自己。比如说啊,邵伟华先生常说,“可以在有利的时间,去有利的地方,办有利的事。”我们通过理性的选择去改变外部环境,让自己生命的道路变得平坦起来,使自己的生活美好起来。另一方面,从主体上来讲,因为你知命,所以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适应变动的环境。比如说算命师跟你讲,你最近可能财富会有丢失……
朱蔚:破财?
陆老师:那么我说你就可以采取相对的策略,比如注意我的投资,我在投资方面更加谨慎一点。相对的讲,你不就是改变了你的命运吗?从自我的角度,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在某一阶段的策略,都是很有效的。
朱蔚:对,还有就是说你破财了,您可能就花个钱报个班读书,这就是财印相破。
陆老师:这也是一个方法。其实真正的知命者他并不唯命。你要了解我们现在的命理学,它的价值观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观,它是以钱财、地位等等方面来衡量你这个八字的高低。就我个人来讲,我一面在研究命,其实我并不认同它的价值观。但是我也知道你脱离了现实的价值观,那命理就没有标准了,是吧?知命者并不唯命。你一个知命者应当努力超越自己的生存情况,敢于超越自己的命运,由人道向天道回归,在有限中去追求和实现无限。当然这是多方面的。历史上最早的命理书叫《李虚中命书》,它里面就说:“出五行之外者,生死在乎我。”其实它就反映了道家超越的观念。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志士仁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是大道的追求,是一种真正的超越。这其实也是中国哲学的真谛所在。
朱蔚:知命也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看山是山的时候,我非常想了解我自己的命理,我的格局,我的喜用,这是第一个层次,您了解了自己的命理;第二个可能是您理解了生命的有限性和必然性;最后就是您体悟天道,像您刚刚说的中国的传统的哲学里面那种天人合一,在有限里面去寻找一种无限的东西。
陆老师:你刚才讲到的是一种禅宗的理念。我们在学禅的过程中,首先是我们看到的是山是水,然后当你的境界提高了,你这个时候看到的不是山也不是水,到了第三个阶段你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一个更高的境地。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可以把它应用到学习八字命理上面去。学习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些基本的概念、一些基本的命理现象出发,分析和剖析它的。在命理教学方面我做的努力,其实就是顺着这个路子走。中国的文化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文化,我把它用西方的方法先进行解构,把这个复杂的命理先化为不同的视角。通过结构剖析,我们了解它不是山不是水,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掌握了一个大的框架的各个侧面以后,接下来再回到具体的一个人生,这个时候就是一种综合了。如果能够把禅宗对文化的一种认识,应用到八字命理解析过程当中去:生命是一个复杂现象,把复杂现象能够条分缕析,找出它的不同的视角,然后再予以综合。这样呢,对于我们学习中国文化,包括命理文化,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朱蔚:刚才说的一部分,人是有能动性的,比如像邵伟华老师说的“有利的时间做有利的事。”这是一部分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二部分是认识了命理之后,怎么去改变自己内心的,一个人生的心态,去完成这一种超越,如果说我现在知命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知命其实是无法改变在世俗意义上的,比如说财官、夭寿、你的格局高低,是不是无法改变他的一个命运轨迹的大框架?
陆老师:对命理学本身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梁湘润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算命只不过是六七十的概率,所以它不是绝对的。因为你想,东汉末年人口只有一千多万,而我们现在八字的排盘,可能有的是五十几万,那么男命和女命的走运方向不同,也就是112万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是很粗略的。所以第一,我们对命运的认识,目前我们的算命方法它实际上还是比较粗略的,具有模糊性。这个梁先生讲的六七十的概率,我个人的体验,有的时候你算得准确的时候,可能八九十都有,但是毕竟这是模糊的剧本,它是平面的;到一个具体角色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是站立的,是生动的。不要被先天的这个测算完全迷信了,若是那样倒真是“迷信”了;就好像说我100%的按照这个做的,不应当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第二,有这样先天的条件,但是你可以去选择和怎么发挥你这个角色,对不对?一个好演员,他有剧本,但是他在舞台上演得生龙活虎的,让你有深刻的印象,那样才是一个好演员。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应该发挥你的主观能动作用,你了解自己的弱点和自己的长处,那么尽量的来扬长避短,是不是?我可以举个简单例子。在1949年我出生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今天我已经76岁,虚岁77岁了。可我还没活不到今天上海老人的平均年龄。如果你说生死是确定的,那么我们同样的命局,1949年和2025年完全不同了。如果你说生死是确定下来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至少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我们可以在选择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去做最适合我们的事情。这才是知命,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一种方法。
朱蔚:老师您有听过一本书,叫做《有限与无限的游戏》吗?詹姆斯卡斯的一本书。李虚中说的“出五行之外,生死在乎我。”这让我想到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观点,他所谓的有限是什么?一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时间,他获得的资源,这些都是有限的,如果你追求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获得成就,那么你就是在玩一个有限的游戏。但是如果你去掉这个有限,你去掉这个边界,你看到的是我要为后人去传达什么?你看到的是这个东西是在于我去定义,我不玩有限的游戏,我创造一种属于自己无限的游戏。您之前裸辞去研究命理,也是在离开有限的游戏,自己创立了一个无限的游戏。去研究命理,把命理学传承下去给后面的人看。
陆老师:说到有限和无限呢,使我想到为什么我会在书上写这句话。因为我小时候接受过很多道德教育,比如说雷锋,他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句有限到无限是当时他讲的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对我来讲,我现在已经这个年龄了,名和利已经非常淡漠了,而我想做的就是利用我现在有限的生命,如果我真能把中国命理史给捋顺了,我不是说是无限,至少我个人的生命就延长了。50年以后,100年以后,若还有人去读这本书,我的生命就寄托在这本书页上,也就延长了我个人的生命。
朱蔚:从有限到无限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挣脱了其实时间对你的束缚性,不追求现实意义中的一种游戏的玩法(追求名和利),那你反而能得到超越这个边界以外的无限的一种快乐,这是一种更属于精神上的追求。
陆老师:是的,好多朋友说:“陆老师,现在嘛人家都是全世界旅游是吧,珍惜这个日暮的夕阳的时代,哎,你怎么老在书斋里面待着?”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现在只能抓住这个晚岁的时间,不知老之将至,有限到无限,我不敢去追求无限,但是我想延长我的实在的生命。这样人活着觉得很有意义。去年75岁了,我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过去可以坚持一天的学习写作,现在吃过晚饭以后就往往觉得很累了。只能珍惜现在的时间,好好的学习和写作,能够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这是我的追求,我的心愿了。
朱蔚:记得我们第一次上课,定的上午是3小时课,但是您一开始讲就兴奋地还拖堂了差不多半小时,快一个小时,停不下来。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您好像对命理学有非同一般的这种热情,一旦讲到命理学的东西,您就不想停下来。
陆老师:是的,我现在这个年龄,连续讲3个多小时确实是很累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上课堂的时候,自己对自己讲,可能要放缓慢一些,或许要保持一点精力能够讲到底。但是真的上去了,好像打了针剂一样,不愿意下课了。因为我真的是热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上了课就往往忘了自己,等下午回到家里后,这个时候真的感到老了,确实是累了。
朱蔚:和您接触下来,您身上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您天生就有的,还是在您接触命理之后发现热爱它才会有的?
陆老师:我可能是小时候受的教育,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学习。后来,语言学本身我也是从无知到有知。那么,现在命理学是我的好奇,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以后可以写这么多书。学习以后确实被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化,包括那些经典著作所迷上了,所以我很想能够传承它。当然,我们现在是整个时代做了很大的变迁而我们过去的命理学,主要是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在中央集权的皇朝的基础上形成的。现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走向AI(人工智能)的社会,我们的命理学也正面临着一个转折、或者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好多事情要做。可惜年纪大了,有好些事情自己觉得力不从心了。比如说对时空基因的研究,主要是想从这个角度去研究人的健康和他先天疾病的因子是否有关。
朱蔚:就是从八字去看他的一个健康程度,先天有没有一些基因上的问题,会容易得哪种病?
陆老师:对的,因为我们现在跟我们的古人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有大数据了。在过去,现代科学在西方有了长足的发展,那么西方的科学,首先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去探索宇宙的一些未知现象,或者说去探索某种真理。但是上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于有了大数据。根据大数据我们虽然不能直接推导出因果关系,但是大数据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相关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可以寻找这个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我们的中国文化或者说命理文化,它更多的是一种大数据的研究。它的结论,更多的是一种概率性的描写和预测。我们有了新的工具,我们有数理统计的工具,有大数据的工具,使我们的命理学可以有新的面貌。因为每一次工具的改革,往往是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节点。所以我寄希望于目前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人,我们要传承,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过去的一些概念,一些经验而受到捆绑,好像跨不出去了。我们应该更多的与时俱进,利用现代的科学工具,对我们传统的这么好的东西做进一步的研究,把它推向前去。
朱蔚:命理学之前的发展,是一种对经验的归纳,到了这个阶段是一种数据上的论证,可以这么理解吗?
陆老师:可以的,因为现在应该采取新的方法。我和一些研究者有时候有些争论,比如说古今的争论,不少研究者他们说我们应该回到古代去,甚至有说近十年来我们的命理学应该是以“复古”作为一个标志。我恰恰相反。我研究古代不是仅为了研究“古”,我研究它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些好东西可以继承。但是我并不主张“复古”。既然时代变了,比如我们古代的职业——士农工商,现在的职业真是多种多样,数不过来了。我现在做的好多研究,我的目的就是用大数据寻找背后的某种规律,某种逻辑,我们把这些逻辑发掘出来,为的是更好地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命理学必须与时俱进,而且已经具有了与时俱进的条件,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去花功夫去收集资料,去进行研究,去寻找它的底层逻辑。说到底,我希望命理学学术化、逻辑化、现代化,能够从原先的江湖走入我们现代的学术殿堂。这是我的追求。
朱蔚:您刚刚说到江湖和学术,其实江湖和学术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争论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命理的知识能传承下来都是靠一代一代的书房派记录下来的。
陆老师:是的。民国时代徐乐吾先生曾经指出过,命理学存在着书房派和江湖派。他觉得蛮遗憾的,在历史上,书房派和江湖派一直没有很好的交流,没有相互的推进。在我看来,没有江湖派的实践,命理学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生命,所以江湖的日常算命活动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反过来讲,没有书房派的总结,我们命理的发展传承就会有问题。你可以看到,我们历史上出现的几本经典著作,比如说古法里面的《五行精纪》,它的编辑者就是一个追求功名而不得的秀才,他是一个读书人,他编辑了这本书。比如说《命理约言》,他的作者陈素庵是清初的相国。比如说《三命通会》,他的作者用今天的话来讲,曾是省军区的高官。这些人都是读书人,他们并不是实际参与江湖的算命先生,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现在才有命理学的历史传承,才有这些经典著作,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研究者的心得和成果。书房派和江湖派应该是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相互交流,这样可以使命理学朝前走,这也是我的初衷。我学习的初衷就是希望它的学术化,这样命理学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命理的实践和命理理论其实并不冲突,它其实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目前有些朋友,他们往往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甚至好像我是江湖的,我看不起你理论的研究。可能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希望“神化”算命活动,因为只有神化了,他就显得更重要了;他也有一种经济利益在里面,我神化了,来向我请教的人就更多了,我的客户群就更大了。从职业的角度,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每一个职业的算命师,他的客户群是有限的。这次我们上课,学员中就有一些职业的命理师。有个问:“陆老师,你怎么书上出现了中将、外交官还有驻外大使,我最高的客户就是个处级干部或乡镇领导。”因为我确有朋友曾是驻美的总领事、驻欧洲某国的大使。这实际上暴露了职业算命师的局限。把实务和理论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不妥当的。我是在构建一个大框架,我们命理学所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人群。人群本身就有干部,或者富人,甚至于亿万富翁,还有众多的普通人群。所以我们研究命理学,你必须要有一个面对大众的大的理论框架。我是从理论上给了你们一个大的骨架,你们根据服务的对象或者说你们熟悉的人群,去填上他具体的各个内脏内容,这样我们才能把命理学学术化,现代化。我们不能把个别的一个小圈子的东西误认为这是一个群体的东西,这样对学术是不利的。我不认为说,理论和实践一定要对立起来,尤其是在我目前的教学材料当中,基础教程、进阶教程和动态教程,甚至更高的纲要,我都是把它组合成一个大的框架。这样我们先把一个大框架掌握了,不断的加入血肉。从另外一方面,我从各种书籍当中去选取了实务的内容,我的教材本身也是包含了实务,也是我近十多年来所追求的一个方向。在十年前你说陆老师你只讲理论不讲实务,那我是同意的;但是今天你讲这个话,我觉得你是不是真看过了我这些教材。
朱蔚:对,您刚刚说那3本教材是非常适合新手入门,从了解命理学的一个历史发展到命理学的框架结构,比如说强弱视角、调候视角、格局视角、形象视角,您分别都讲到了,因为它可能是在不同的书里面提到过的。把一个大的框架打好以后,大家在实战的时候发现自己更适合用哪些,再把它填进去。
陆老师:是的,我做的这个工作是从历史的源头开始的,我们不像学习中医有一本《黄帝内经》,它在理论高度上,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大框架。我们现有的《子平真诠》,它着重于格局的研究,比如说《穷通宝鉴》,它着重于调候的研究,比如说《滴天髓》,它更多的包容了变化的诸多现象。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些经典著作,把它容纳到一个大的体系当中去。我们要用现代科学的观念去看待命理学。可能有些朋友不一定会赞同我的说法,但是我们的教育在进步,观念和想法跟古代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写的教材目的就是想更快地、更容易地让现代人去入门去研究,这样命理学就有了基础,可以更好的向前发展。
朱蔚:我们这个班上有几个非常职业的命理师了,但是他们每个人服务的对象,客户群体都完全不一样,用户画像完全不一样,有一些是偏门的人找他比较多,有一些可能互联网从业人员找他比较多一点,有一些可能做生意的人找他比较多一点,不同的命理师,他们的用户群体,他们的服务对象不一样,所以他们能积累的一些命例,推出来的“象”其实是非常局限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象,但是这些独象是不能成象的,你应该把象背后的这个理给揪出来,然后我们系统地逻辑地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陆老师:你说的倒真是在要点上。中国文化往往兼具“象、数、理”的内容。有的时候夸大了象的作用,因为象跟客观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它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个象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你从象的角度去把不关联的东西联系起来,有时候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效果,或者说对你的客户来讲怎么这么神准?我不是否认象的作用,它确实很重要,尤其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因为我们强调了相关关系,那么象就是一个介体;但是象有它的局限性。命理学成为一门学术,更重要的是要挖掘象背后的底层逻辑。在“象、数、理”三者之中,我很强调最后的这个“理”。这是为了受教育的人容易理解,容易入门。你把理讲清楚了,他们就觉得能够掌握。老是在讨论“象”,把他们弄得云里雾里。他们觉得你讲的都对,但是我不会用。我的做法就是怎么使它逻辑化、通俗化、现代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我们向前发展。
朱蔚:您写的三本基础课程就是我们学习命理时刚开始需要的拐杖,只有在拐杖柱稳了以后,你才能把拐杖扔掉,基础打稳了以后,你才能发现它背后的某种“象”的联系。
陆老师:你说对了。孔子讲“登东山而小鲁”,因为我们登山的足力不够,所以我提供某些分析的方法,其实都是拐杖,它们是帮助你去理解,在爬山的前期你的足力不够,那么有了拐杖你可以比较相对轻松的攀上东山了。但是毕竟孔子讲的登东山而小鲁只是鲁国,他又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我的教程是帮扶你登上东山,但是真正要爬上泰山,那就需要自己的努力了。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阅读古代的经典著作,你就要通过大量的现代案例的实践,当然也要读我们目前的不同的派别的书本,每一本书都有它的长处,我们现在有格局派、强弱派和盲派等存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盲派,主要是段建业、邢敏芬他们写的书。段老师的书上谈到盲派不要格局,不讲强弱等等,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标帜性的,带有广告性的言辞。因为真正谈到财的问题,你不谈强弱,你怎么来讨论这个人富有或不富有;或者财在他手上,还只是一个来去的流水?当谈到财的时候,他又要讲强弱了。作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下去的一个完整理论,你脱离不了历史上对格局的研究。我把格局看作是一个八字结构当中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格局没有破坏,再加上有用神的话,我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在人群的层次上面,如果我们分三六九等,可以说他已经具有第五等的或者中产阶级的层次了。如果用神得力还有其他要素的加入,他就可能跨越中产阶级到上层去。在研究人的社会层次方面,格局确实具有很高的标识功能。轻易把古人的东西,把它当一个破鞋丢掉,我觉得太可惜了。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心理或者自己论命的经验,但是往往你要打开你的思想界限,这就是我希望学术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朱蔚:我听下来,您对命理学是非常一个包容的状态,您会认为不管是实战的,还是研究的,是格局的还是强弱旺衰的,或者是专门抓象的,它里面都是有好的地方可以获取,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学习完整框架之后,挑选对自己最适用的。
陆老师:在实战教材上所罗列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大框架。你在进入一个学科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大致了解,一下子就钻到了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去,对的,这个研究项目有它自己独特的东西,你钻下去没错。但是你有大框架的概念,你就有比较大的视野。这个视野对你学习是有触类旁通的作用,使你会觉得更全面,使你可以更深入。我们不能忽略实践,但是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往往会走样的,而且是不深刻的。
朱蔚:所有的实践其实最后还是得提炼在这个理法。
陆老师:是的,对于今人一些研究,对于古人的研究,我们都要关联起来,你有了大的背景知识,对你具体去研究某一个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
朱蔚:很多年前您就写了《又一种基因的探索》,应该是最早的通过计算机输入八字信息、进而预测疾病可能性的一本书。
陆老师:在这方面,我很希望能做现代的应用研究。我们今天既有条件又有工具,我们可以一个课题、一个课题的去做研究。我们目前用的子平法的模型,我称为“今法模型”。它或许也能称为是一种个人先天的“时空基因”。我实际上做的就是类似的研究。我一开始从体质下手。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提出中国人的九种体质,那么我就收集了大量的案例,请他们填写王教授的体质检查表,大概有60个问题。然后归纳出你大概属于哪一种体质。我接着再把他们的八字做分析,最后我确实找到了对应关系。这是一个方面。后来我进一步研究疾病,找了900多个案例,大约7种常见疾病。我也用同样的方法经过计算机分析。我用的是一种叫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的方法。最后我找出你的八字的先天结构,你可能发病的概率就有了一个序列了。比如我自己,心脏病、高血压就会显现出来。当然我现在的案例还不够,如果我们能依靠大数据得到使人信服的结果,对我们的养生保健,就可以发挥后天的主导作用。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现代化课题。再进一步讲,我曾经研究过大概不不到400例的癌症病人的先天时空结构。我发现除了这个疾病的相克关系是主导关系,比如说他是肝病,肝属木,那金是肺,金可能能量很大,而肝的能量很弱,于是金克木,这是个体发生肝癌的一种统计的结果。一种主导现象被揭露出来了。另外一方面,我还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癌症病人,我用统计的数据把它制成一个图表,这个图表有十个因素,即十个天干,比如甲乙,甲是阳的,它代表胆;乙木是阴的,它代表肝。癌症病人的那张图一共是5对阴阳天干,往往其中有3对阴阳呈现出较大的对立状态。如果我们能够收集3000个案例来做这样的研究,能够发现确实一共5对当中,有3对是上下对立的。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对癌症的描写,就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预测了。需要收集这样的资料,来做这样的统计,很可惜我找不到可以合作的中医学院或中医研究所。如果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来做这样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一方面可以打破我们所谓的八字命理是迷信的观念,另外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这么好的,只落在江湖中的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走入学术殿堂。我做这样的研究,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你拿案例来,大数据时代有一句最重要的话:“除了上帝之外,我们应该拿数据来说话”。我是遵从这样的信念的,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能不能赞同。
朱蔚:老师,我觉得您是看了很多命理书,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归纳出了自己的论命体系,但您有担心归纳的不一定对,所以会去统计很多的案例,通过统计的方法去论证归纳的经验性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正确。
陆老师:是的,刚才你曾经提到的现代科学,他们发展起来主要是抓住了因果关系。爱因斯坦做过一个总结,他说主要靠的是两条,一条是亚里士多德、希腊古代一直向现代发展的一种逻辑的认识,它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对于具体现象你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因果关系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石。第二,实验,科学到了近代发展了实验,任何事情要通过实验来证明,实验证明了你才能够成立。这是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路。但是爱因斯坦也惊奇,他说中国人没有遵循这两条,他们也获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比如说四大发明,很多技术上的突破。过去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这个惊讶,好像大家都说不上一个理由来。但是现在大数据时代来了,我们对真理的探索可以是因果关系的,也可以是相关关系的,也就是大数据。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我们又有运算工具了,我们有计算机,一个很复杂的计算,本来你要做一生的事情,可能计算机两分钟就帮你解决了。
朱蔚:对,现在八字排盘很方便。
陆老师:盲人掐指是过去的绝活,他能够掐着手指把你的八字排出来,但是现在这样的程序太多了,一两秒钟就把你的八字排出来了。随着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有了研究的广阔天地,你刚才问我是经验的还是完全是一种逻辑的?现在的大数据实际上就是在经验方面扩大了它的功能,大数据可以为我们证明或者证伪。如果你讲的不对,大数据做出来并不符合,那就是证伪了。我用的数量研究的方法是公开的,我没有任何保密,研究过程我可以告诉你,那么你收集资料,如果你能证伪,那也是很好的事情。
朱蔚:是的,这是科学朝前走的发展过程。老师我总结您之前做的这些事情,我发现挺有趣的,编著的中国命理学史论它是追溯历史的一个东西,您编的命理学的基础教材3本书是针对初学者想要入门的人,有一个大的命理框架,包括你做的这个实证项目,做基因探索医疗相关的,是给别人看病的,好像这三样都是利他的东西。
陆老师:我是从好奇开始的,由好奇而研究,由研究而成为好像自己身上负有的一种历史使命。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想,或许有些人不同意我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我的追求而言,就是希望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现状、通过做实验,想把命理学,想让这位已经有千年生命的老人进入学术殿堂,成为一个年轻人,重新出发。我做的三方面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目的:一个方面是历史,我们不了解历史,不了解传承,我们怎么朝前出发?一个是教学,如果我们不能去推广这样的教学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学问又怎么发展?一个是具体的项目,如果我们不展现它对我们今天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这个学问它的目的、它的方向就不能展现出来。所以根本上来讲,我很热爱中国传统命理,我愿意尽自己个人的努力,当然这个努力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是尽力了。
朱蔚:您之后有新书的计划吗?
陆老师:从去年开始,我打算重新再写一本命理学史,《命理学史论》和《命运的求索》,我当时是带有实用的观念去写作的。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子平法的兴起,以及子平法它具有的框架,它的分析条理等等,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是从推演方法的角度把它串联起来的。现在有好多人说:“陆老师,我是读了《命运的求索》才喜欢这个东西的,才入门的。”说老实话,我也很惊讶;我当时并没有这个目的。作为一本入门书,我只是去捋了一下,对今天你入门要学习的东西。我是把它这个线索捋清楚了。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回过来,历史过程当中对古法是忽略的。正因为前几年有古今之争,我参与了争论,它也是对我的挑战。我重新把古法的十几篇著作一本一本读下来,我也追究古法为什么会被消隐。我用“消隐”两个字,也就说它离开主流命坛的原因。我现在具有这个条件了,从文化的角度再打算写一本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命理学通史,主要就是把它理成一个连贯的历史,揭示它为什么会发展的文化原因。这是我目前打算要下功夫的一本书,或许也是我现在这个年龄,自己觉得精力不济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那么我干脆就从研究历史开始到写一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命理学通史来关门吧。
朱蔚:对命理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陆老师:第一、你要树立一个正确的命理观,是吧?我们研究命理首先的认识不是宿命论,不是封建迷信。如果你带有这样的成见,那你就很难入门了。第二、你可以从今天的一些教材读起,了解命理学一个大的框架。你再读一些现代人专门的研究著作,了解怎么联系实际,同时你自己要注重实践。你把自己、你的亲人、你周围的人——你比较了解他们的一个生命过程,把他们作为案例,按照你学到的方法去进行剖析。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新人,首先你在观念上树立正确的命理观,第二你最好能够找一本入门的教材,第三你要联系实际,当然最后你最好能够读几本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深化你的认识,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想法。
朱蔚:您刚刚有说到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就是老五篇这些都推荐?
陆老师:如果真的要研究经典,这老五篇确实是不可少的。这个所谓的老五篇就是《渊海子平》、《三命通会》、《子平真诠》、《穷通宝鉴》和《滴天髓》。这个老五篇可以给你有比较厚实的命理学的一些基础。
朱蔚:再次感谢陆老师,之前觉得陆老师做的工作是非常多项的,但刚刚跟他聊完之后,发现他做的所有事情,核心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就是他想让中国命理学可以进入学术殿堂的大门,可以让我们把它传递下去。我想借用胡适的一句话“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命理学从古至今,从一代又一代人的手里接过来,一寸又一寸的探索与精进,传递至今,它一直都在通往学术殿堂的路上。
希望这期谈话可以对大家有帮助,评论区可以分享你学习命理时的困惑和思考,抽一位同学赠送陆老师的《命运的求索》。再见。
陆老师:再见,以后有机会我们大家一起交流,谢谢大家。
(2025年6月24日上海)